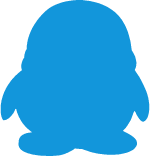《紅豆》結緣
台灣師範學(xué)院的教學(xué)樓裡(lǐ),下課的鈴聲清脆地響起(qǐ),甯靜的校園立馬就(jiù)熱鬧起(qǐ)來了。
教室内,一位女教授放下了講義,面(miàn)對(duì)大家端莊地說(shuō)了聲:“諸位再見!”當她收拾好(hǎo)講義,端起(qǐ)茶杯,正準備離開(kāi)講台時(shí),卻又有一群好(hǎo)學(xué)的學(xué)生圍了上來。
一位女學(xué)生首先開(kāi)了口,她的臉上洋溢著(zhe)崇拜之情:“老師,我是來旁聽您的'新文藝習作'課程,感覺真的很不錯!”
原來,剛才她和一些同學(xué)都(dōu)是站在教室邊上旁聽的。
窗外人群漸漸多了起(qǐ)來,嘈雜聲如潮水般湧了進(jìn)來,使得談話聲似有似無,但他們依然熱情地圍繞著(zhe)這(zhè)位衣著(zhe)素樸的女教授,不忍離去。
這(zhè)位女教授就(jiù)是謝冰瑩,任教于台灣師範學(xué)院,主講新文藝課程。

謝冰瑩居士在台灣留影
因爲遭受日本殖民統治達五十年,很多台灣人除了日語和閩南語之外,基本不會(huì)聽普通話,而一班學(xué)院人士對(duì)于白話文文學(xué)又抱著(zhe)輕蔑和嘲諷的态度,他們對(duì)謝冰瑩在大學(xué)裡(lǐ)開(kāi)設的“新文藝習作”課程進(jìn)行公開(kāi)的責難,說(shuō):“白話文還(hái)用得教?真是太可笑了!難道(dào)'你的''我的''的''了''呢','大狗叫(jiào)''小狗跳'還(hái)不知道(dào)寫?”不過(guò),謝冰瑩不爲這(zhè)些人所幹擾,她的新文藝課程受到了學(xué)生們的熱烈歡迎,當時(shí)不但她所教授的班級全選修了該課程,很多其它班級的學(xué)生也前來旁聽。
圍著(zhe)謝冰瑩的還(hái)有一位衣裝外貌明顯與衆不同的人物,他就(jiù)是出家人性如法師。
“和尚也來學(xué)寫小說(shuō)嗎?太奇怪了!”有人這(zhè)麼(me)問。
謝冰瑩回答說(shuō):“爲什麼(me)他不能(néng)學(xué)著(zhe)寫小說(shuō)呢?多少佛經(jīng)上的材料,可以改寫爲故事(shì)、小說(shuō)、戲劇的。據我所知,所有宗教裡(lǐ)面(miàn),佛經(jīng)是最深奧的哲學(xué),有人窮畢生之力去研究它,也不能(néng)有多少成(chéng)績。”
聽到謝教授如此地贊揚佛教,性如法師真是高興極了!待大家離去之後(hòu),性如法師特意請求與謝冰瑩同行,他還(hái)有很多話要和謝教授交流。
他說(shuō):“謝老師,汐止的彌勒内院,有一位高僧慈航禅師,您見過(guò)嗎?”
“沒(méi)有,隻是在報上看見過(guò)他的名字,想必你一定認識他。”
“我是他的學(xué)生。他老人家是一個道(dào)德高尚、學(xué)問淵博、待人和藹、誠懇的大好(hǎo)人,您不可不認識。”
實際上,這(zhè)位性如法師是大陸來台的學(xué)僧。
1949 年,很多佛學(xué)院的辦學(xué)受到影響,部分學(xué)僧彷徨無措,不知何去何從,加之囊中羞澀,個個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。
這(zhè)時(shí),性如所就(jiù)讀的佛學(xué)院收到了台灣慈航禅師寄來的挂号信,信中說(shuō):“諸位同學(xué)們的來信,我都(dōu)收到了,隻可惜遠隔重洋,我不能(néng)把你們每一位同學(xué)都(dōu)接到台灣來,現在我希望各同學(xué)自己設法來,一切住處飲食,我都(dōu)可以保障。”
學(xué)僧們收到慈航禅師的信件都(dōu)興奮不已。
性如曆盡艱辛來到了台灣,在戒兄的指引下見到了慈航禅師,并留在彌勒内院跟随法師修學(xué)。1952 年秋天他就(jiù)開(kāi)始來師範學(xué)院聽謝冰瑩的課程,整整一年,風雨無阻。
“我想一定會(huì)有緣認識他的。可是我太忙,不知道(dào)要什麼(me)時(shí)候,才能(néng)抽出工夫來。”謝冰瑩心裡(lǐ)有一些拒絕的意思,但性如法師依舊熱心地邀請,他說(shuō):“從台北東站,搭往基隆的車,到汐止站下來,隻要二十多分鍾,再步行十分鍾左右就(jiù)到了;最好(hǎo)上午十點左右去,在山上吃了午飯就(jiù)回來,隻要耽誤半天就(jiù)可以了。”
“好(hǎo),下次去時(shí),我通知你,請你做向(xiàng)導。”
“還(hái)有”,性如法師接著(zhe)說(shuō),“彌勒内院的下面(miàn),有一個靜修院,那是比丘尼修行的地方,環境幽靜極了,真是個寫文章的好(hǎo)地方,您在寒假、暑假中間,可以住到那裡(lǐ)去寫作,包您會(huì)滿意的。靜修院的當家師達心法師和一位呂太太是幾十年的老朋友,您如果去住,隻要呂太太介紹一下就(jiù)可以了。”
“有什麼(me)手續嗎?”
“沒(méi)有什麼(me)手續,不過(guò)要在那裡(lǐ)和她們一塊兒吃素,您住多少天,随您的意,走的時(shí)候,給一點香火錢就(jiù)可以了。”
這(zhè)次與性如法師的交談,使得謝冰瑩心中牢牢記住了兩(liǎng)件大事(shì):第一是要拜訪慈航禅師,第二是要去靜修院寫文章!
也正是有了性如法師的因緣,謝冰瑩才與佛教有了較多的接觸,但此時(shí)的她,确實是一位佛教的門外漢,對(duì)于佛教經(jīng)典一知半解,于佛教可謂是敬仰有餘而親近不足。
一直到了1953 年,因爲受到小說(shuō)家傅紅蓼的請求在其創辦的中學(xué)生刊物《讀書》半月刊上連載長(cháng)篇小說(shuō),她開(kāi)始進(jìn)行長(cháng)篇小說(shuō)《紅豆》的寫作。
《紅豆》的寫作是有感于當時(shí)台灣特殊的社會(huì)環境,她希望通過(guò)小說(shuō)強調戀愛是神聖的,絕對(duì)沒(méi)有階級、貧富的限制;同時(shí)要使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感情融洽,打成(chéng)一片。但這(zhè)部小說(shuō)的寫作可謂曆經(jīng)波折,謝冰瑩這(zhè)位大才女也遭遇了文思枯竭、一個字也寫不出的窘境。
因爲文章寫不出,傅先生又頻頻來信催促,謝冰瑩著(zhe)急地在房子裡(lǐ)打轉,自言自語地說(shuō)道(dào):“有鬼!這(zhè)一定有鬼!爲什麼(me)寫不下去呢?是孩子們太吵嗎?他們都(dōu)上課去了,爲什麼(me)不能(néng)寫呢?過(guò)去許多文章,不也是在這(zhè)種(zhǒng)環境裡(lǐ)寫成(chéng)的嗎?”
忽然,她得到一個啓示:要向(xiàng)觀世音菩薩求救了。
慢慢地,她安定下自己的身心,兩(liǎng)手合十,閉上眼睛,喃喃地祈求:“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呵!媽媽說(shuō)您是萬能(néng)的、有求必應的,請您賜給我靈感,賜給我智慧,讓我把《紅豆》寫完吧,我會(huì)永遠感激您,信仰您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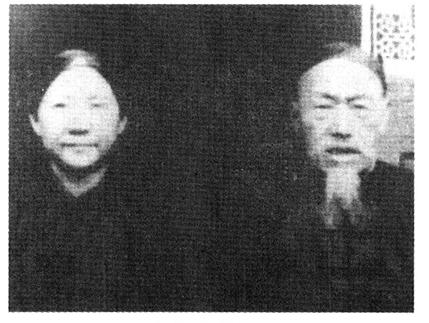
謝冰瑩居士父母
謝冰瑩的母親劉喜貴,是一位堅強、勤勞而樂于助人的女人,也是一位典型的傳統禮教教育出的婦人。她出生于湖南安化縣羅家灣,早年就(jiù)承擔起(qǐ)家庭的重任,讀過(guò)《女兒經(jīng)》《烈女傳》等女學(xué)讀物,能(néng)略微識字。據說(shuō)因爲慷慨好(hǎo)施,且喜歡打抱不平,她在村中深受信任,有著(zhe)很好(hǎo)聲譽與威望。大概是因爲母親在遭遇艱難之時(shí)時(shí)常念誦“觀世音菩薩”名号,給幼小的謝冰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以至于她在遭遇困難之際也自然想起(qǐ)這(zhè)種(zhǒng)方法。
祈求完畢,一個念頭掠過(guò)她的腦海:到靜修院去寫,一定能(néng)夠一氣呵成(chéng)。于是立刻整理簡單行裝去中山北路找呂太太,這(zhè)時(shí)已經(jīng)是晚上八點多了。
到了呂太太家,隻有一位小姑娘接待。呂太太已經(jīng)外出去基隆了,要很晚才能(néng)回來。
見到呂太太的書房裡(lǐ)供著(zhe)觀世音菩薩像, 謝冰瑩的雙腿很自然地下跪, 然後(hòu)竟不顧自己是在别人的家中, 從小箱子裡(lǐ)取出稿紙, 在客廳裡(lǐ)俯身就(jiù)著(zhe)矮桌上寫書了。說(shuō)也奇怪, 這(zhè)一寫就(jiù)是兩(liǎng)千多字, 文思如潮湧源源而來……
門鈴響了,進(jìn)來的是性如法師。小姑娘已告知他謝冰瑩到訪因此特意趕來了。
性如法師進(jìn)來不久,呂太太也回來了,她一見陌生的謝冰瑩大爲驚訝:“這(zhè)麼(me)晚了,您來有什麼(me)貴事(shì)嗎?”
“請您陪我去靜修院。”
“太晚了,她們恐怕早睡了。”
“沒(méi)有關系,我們可以叫(jiào)開(kāi)門。”
“爲什麼(me)非在今晚去不可?”
于是謝冰瑩把在家寫不出文章、許了願之後(hòu)就(jiù)寫出來的事(shì),一五一十地告訴她,并說(shuō)已下了決心,今晚非去不可。
“這(zhè)麼(me)晚了,又是下雨,那條小路,恐怕不好(hǎo)走。”呂太太面(miàn)有難色地說(shuō)。
“不要說(shuō)下雨,即使下雪、下刀,我也要去!”
呂太太聽到這(zhè)裡(lǐ),便不再阻止,馬上動身。
性如法師自告奮勇地送她們到靜修院的門口,就(jiù)獨自一人上山了。
說(shuō)也奇怪,原本“江郎才盡”的謝冰瑩一到靜修禅院就(jiù)變得文思泉湧,很快就(jiù)完成(chéng)了《紅豆》的創作,她不由得對(duì)菩薩的感應充滿敬信!
上一篇
下一篇
(作者介紹:本性禅師,福州開(kāi)元寺方丈、泰甯慶雲寺住持)




 我要投稿
我要投稿 返回大同市南郊區清涼寺首頁
返回大同市南郊區清涼寺首頁 返回資訊頻道(dào)
返回資訊頻道(dà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