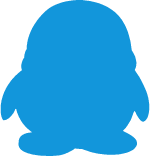入台印象
1948年7月13日,一艘航船緩緩駛進(jìn)台灣高雄港。
高雄,曾被(bèi)傳教士們稱爲打狗(Takow),自古就(jiù)是閩台兩(liǎng)地船隻往來的重要港口。
應寶島台灣中坜圓光寺妙果和尚之請,慈航禅師輾轉從新加坡啓程途經(jīng)廈門乘船二十餘日抵達高雄,開(kāi)始了入台創辦台灣佛學(xué)院的曆程。
入台之前,慈航禅師在1947 年五十三歲壽誕(八月初七日)前結束了爲期三年的閉關(楞嚴關)。
三年關中,慈航禅師每日放焰口及講課,還(hái)創辦《人間佛教》《佛教學(xué)校人間》及《馬來亞素食特刊》等中英文月刊,流通歐美各國(guó)。
出關之後(hòu),慈航禅師在馬來亞各地組織佛學(xué)會(huì)并努力地弘法。《學(xué)僧天地》第一卷第五期消息《慈航法師將(jiāng)赴台灣創辦佛學(xué)院》雲:“慈航法師在南洋閉關三年,業已期滿,正行腳馬來亞各地組織佛學(xué)會(huì),俟該地工作告一段落後(hòu),將(jiāng)應台灣佛教界之邀,前往創辦台灣佛學(xué)院雲。”而星洲《佛教人間》第5 期亦提及:“本社社長(cháng)慈航法師,出關以後(hòu),弘化工作甚忙,已于本月十六日離星,往各處弘法,現已安抵吉隆坡雲。”
出關之後(hòu)的慈航禅師确實是“弘化工作甚忙”,他曾經(jīng)寫信給弟子護法童子說(shuō)及自己的工作安排,他說(shuō):“上午八至九唯識,九至十覆講;十至十一五蘊,一至二覆講;下午二至四通俗,七至八覆講;星期二、四、六下午二至三時(shí)半則在菩提學(xué)校講四書及佛學(xué)。餘身雖忙,而心甚愉快!大約七月間可赴台灣、南洋各地工作,可由各自負責。”該信函中慈航禅師不禁有“餘老矣”之歎,他還(hái)勉勵弟子們要報四恩,及時(shí)努力。
在忙完了南洋各地的弘法工作,交代好(hǎo)南洋的事(shì)務之後(hòu),慈航禅師準備應邀入台了。
台灣,這(zhè)顆祖國(guó)美麗的寶島,慈航禅師也是第一次踏上這(zhè)片土地。
慈航禅師在《我所見到的台灣》一文中欣喜地描述了自己入台的所見所聞所感,他說(shuō):
久聞台灣是樂土,非親眼看見是不大相信,由一個機會(huì)給我由南洋送回這(zhè)親愛的台灣,數月來所見到所聽到所知道(dào)的一切的一切,真是出人意料之外——稀奇!
隻從兩(liǎng)方面(miàn)來講:一、民間的和樂。由廈門乘船一到了台灣的高雄,再乘大車到了我們的目的地——中坜鎮,第一個印象,所看見的遍地都(dōu)是黃金,那時(shí)正在割稻田,遍地都(dōu)是稻谷,沒(méi)有一塊是荒墟的空地,除了稻田之外,那就(jiù)是蔗田——黑皮甘蔗,哪怕就(jiù)是一個小角落,不是種(zhǒng)番薯,便是種(zhǒng)蔬菜,台灣米和台灣糖,是久聞于世的,不但是能(néng)自給自足,尚能(néng)供濟外省,生活是民生的大計,是人民不可少的大前提,而台灣可算是能(néng)將(jiāng)此大前提解決了!“台灣之地豐富,台民之勤勞”在這(zhè)兩(liǎng)句話裡(lǐ)面(miàn),可以做台灣的寫照,當之無愧。
其次,不但台民的勤勞,可以作我們全台人的模範,他們那種(zhǒng)樸素和禮讓,也就(jiù)能(néng)感動人心,除了少數人衣冠較華麗外,而十之八九,都(dōu)是穿著(zhe)土産,很少有洋化,尤其是我們在火車上,群衆的聚集場,不難看見他們那種(zhǒng)禮節,都(dōu)可以代表台灣的民風,我不能(néng)用什麼(me)語言來形容它,隻好(hǎo)說(shuō)一句,恐怕是桃花源裡(lǐ)面(miàn)的人物吧。
慈航禅師的激動不僅僅在于初次入台,而在于回到了自己親愛的祖國(guó)——寶島台灣自古即是中國(guó)領土的一部分,清末因爲政府的無能(néng),台灣被(bèi)日本占領,直到1945 年10 月25 日,國(guó)民政府任命的台灣省行政長(cháng)官陳儀宣告:“自即日起(qǐ),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(guó)版圖,所有一切土地、人民、政事(shì)皆已置于中國(guó)主權之下。”被(bèi)迫割讓50 年又156 天、飽受蹂躏的美麗台灣重歸祖國(guó)。
回歸祖國(guó)的台灣,人民安居樂業,民風依舊樸實,這(zhè)自然是令人倍感振奮的!慈航禅師繼續寫道(dào):
佛徒的廣泛。上面(miàn)的是台民的本質——豐富、勤勞、樸素、禮讓……大概說(shuō)了一點,至于佛教方面(miàn),又是怎樣(yàng)呢?聽說(shuō)台灣大的人口,有三分之二,都(dōu)是佛教徒,這(zhè)在家庭中樓上樓下,所供的佛像,就(jiù)可以看得出來的。見了佛像禮敬,看到僧尼鞠躬,一見之下,就(jiù)可以知道(dào)他是一位佛教徒,尤其是台灣的佛教,有一種(zhǒng)特别的風味,每一個寺廟有一個組織,叫(jiào)做信徒總代,他們做到這(zhè)信徒總代,也覺得非常的光榮,對(duì)于他這(zhè)個寺院裡(lǐ)的一切的一切,好(hǎo)像自己家裡(lǐ)的事(shì)情一樣(yàng),盡心盡力去幫助,這(zhè)就(jiù)是我從前在南洋人間佛教月刊上,提倡過(guò)中國(guó)的佛教,每寺廟要組織一個護法團來維護佛教,免得寺産任人摧殘,僧尼被(bèi)人欺侮,誰知在台灣這(zhè)塊樂土,早已實現了,所謂先得我心,尤其是女衆的寺廟較多。
現在所發(fā)現台灣佛教的風氣,就(jiù)是人人愛求學(xué),并不是寄生式的、暮氣沉沉、死後(hòu)往生的,是靈活的,是活潑的,是佛教人間的,我隻希望一班大德起(qǐ)而提倡,將(jiāng)台灣整個的佛教來振作一下,這(zhè)成(chéng)績一定是大有可觀作全國(guó)佛教的模範省。
這(zhè)當中論及台灣的佛教。慈航禅師以外地人的敏感來觀察台灣的佛教,其中主要有兩(liǎng)個方面(miàn)值得注意:一是信佛的普遍,所謂台灣家庭中樓上樓下都(dōu)供佛像,這(zhè)還(hái)是保留著(zhe)明清以來台灣的傳統;二是有一種(zhǒng)特别的風味,這(zhè)就(jiù)主要是台灣佛教組織或團體與大陸傳統叢林的差異,包括僧人的“人人愛求學(xué)”,這(zhè)明顯是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了。
對(duì)于後(hòu)者,慈航禅師有著(zhe)特别的關注,畢竟這(zhè)是他一直的主張,在他離開(kāi)星洲前往中國(guó)台灣時(shí)發(fā)表的《臨别贈言》中即明确地說(shuō):
然而努力要從兩(liǎng)方面(miàn)去做:一方面(miàn)是聯合教團共同去做,一方面(miàn)還(hái)要個人努力。例如:有許多事(shì)情自己一人做不到,那非要群策群力不可。但是,人心不同,各如其面(miàn),有許多事(shì)大衆是不會(huì)一緻的。那麼(me),隻要你認爲這(zhè)件事(shì)對(duì)佛教,對(duì)國(guó)家,對(duì)社會(huì),對(duì)人群,是有利益的話,縱然得不到别人同情,不妨自己去負責,“認定目标,有進(jìn)無退”。所以平常我對(duì)于佛教團體,非常贊成(chéng)!
作爲初次來台的客人,慈航禅師眼中的台灣充滿朦胧的溫情與美感,這(zhè)是人之常情。然而台灣風俗人情的演化實在是一部厚重的充滿辛酸血淚的曆史,台灣佛教之所以呈現出此時(shí)的風貌,也經(jīng)曆了漫長(cháng)的曆史演變。
慈航禅師雖然對(duì)回歸祖國(guó)之後(hòu)的台灣佛教充滿了期待,對(duì)台灣的在家、出家佛教徒給予了極大的希望,然而現實總是複雜而多變的,台灣也并不是所謂的“桃花源”,他在台灣的境遇絕不會(huì)是一帆風順的。
大陸僧侶的來台弘化,慈航禅師并不是第一人。
日據時(shí)期福建僧人特别是與鼓山法系較有因緣的僧人入台較爲普遍,其中最著名的就(jiù)有虛雲大師、圓瑛大師等。
台灣僧伽教育,台灣佛學(xué)院的創立也不是開(kāi)風氣之先的。日據時(shí)期,台灣僧伽教育已有所開(kāi)展,如1917年4月正式開(kāi)學(xué)的台灣佛教中學(xué)林就(jiù)是台灣佛教史上第一所正式的佛教學(xué)校。該校由日本曹洞宗僧衆開(kāi)辦,得到了善慧法師、本圓法師、齋教先天派、台南開(kāi)元寺等的大力支持,學(xué)制三年,其中出家僧侶和在家信徒各占一半。該校學(xué)生在中國(guó)台灣讀完三年之後(hòu)還(hái)可以編入日本山口縣曹洞宗多多良中學(xué)就(jiù)讀四年級,畢業後(hòu)優秀者可以進(jìn)入駒澤大學(xué)深造。
上一篇
下一篇




 我要投稿
我要投稿 返回大同市南郊區清涼寺首頁
返回大同市南郊區清涼寺首頁 返回資訊頻道(dào)
返回資訊頻道(dào)